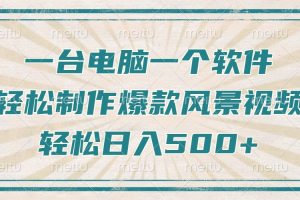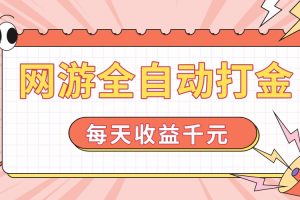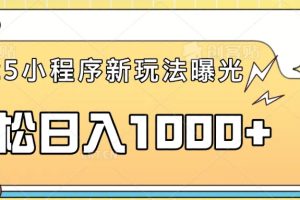是怎么骂的,这里就不重复了,无非是恨国、扭曲历史之类。不重复单纯是因为,复读的太多,大家应该也都听烦了。这里只讨论电影本身的事儿。
先说下我个人的打分吧。以《战狼2》为参照,如果《战狼2》可以打7分,我觉得《八佰》打8.5分问题不大。
就是说,如果你是奔着值回票价的想法,还是很推荐的。
题材方面,《八佰》选择了近几年比较少见的抗战正面战场,讲四行孤军留守上海的故事。
故事发生地主要集中在四行仓库,并时不时延伸及一河之隔的租界区。租界区各国游人如织,四行仓库外头日军环伺,里头待着近500守军。人员密度和戏剧冲突,都被压缩到一个极小而封闭的空间里,顿成剑拔弩张之势头。
到了晚上,一边是夜黑沉沉,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困兽犹斗,一边纸醉金迷。这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对比,用团长谢晋元的话说,就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域”。
这种空间安排,不仅沿袭自史实,实际上也烘托出本片的一个核心主旨:看戏。
应该说,从起手的布置上,管虎做得非常成功。
看
在导演的展现里,看戏是个核心话题,不仅贯穿整个战局,见诸苏州河两岸,并且上升为一种哲学,一种类似于国民性的东西。
河这边是自己同胞在抵抗外侮,导演运用错杂的方言,令同胞这个概念进一步具象化。
四行守军里,有东北来的,有山东来的,有广东来的,有陕西来的,天南海北,共聚一堂。走到一起是为了抵御日寇,保卫那个大家想象中的共同体——中华民族。
河岸的另一边,同样也是同胞,多数时候却只是看,和感动,去承载这样一种被保护的道德压迫。导演甚至还非常露骨地,借一名孩童之口说,叔叔是在保护我们。
四行孤军的奋战究竟算不算保护,自然会有争议空间,但无疑霎时间将租界的国人放到一个极低地位:对面天南海北的人都在为民族危亡奋战,你们就这么看着,就这么心安理得地,充当一名看客。
在危亡关头充当看客,这里头不仅充斥着冷漠,同时被赋予了智识层面的低劣:斗争的英雄是崇高的,崇高不止因为行为本身,还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觉醒。
而看客们则处于一种未觉醒的状态,需要被点燃,被唤醒,被启蒙。于是导演再次借何香凝之口,评论四行守军曰国人个个如此,何愁敌不破。这话很有些皮里阳秋的味道,是在夸四行,其实也是在揶揄看客。
几个比较近的视角,小端午,小湖北,也是在看,看身边的守军如何把戏唱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思想转变。之前吵吵着要跑,后来甘心牺牲,而端午也确实牺牲了,终于由看客变成英雄,成为戏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电影还塑造了一位拿照相机看的记者,拿望远镜看的教授,打窗户口看的妓女……
大家都是远远地看,从而令四行孤军的卖命抵抗更像是一场街头秀。
但考虑到看的情境和时空,“看”就不只是“看”了,而是一种被指摘的麻木。随着战局转惨会愈来愈浓厚,并在几个以身殉国的英雄们几连跳时达到高潮。看客们被英雄们的牺牲而震撼,而热泪盈眶,与此同时导演对看客行为的贬损也到了极致。
戏里另一出情节,小端午顺着河流逃跑,却被目睹英勇抵抗的看客们高声欢呼着捧回来的剧情,加剧了“看”这一行为的残酷性。
同行的另一位同胞,厚着脸皮还要继续往前游,被岸上英人警告军人不准上岸,只能灰溜溜回去,就更是残酷到无以复加:
原来看客们的感动不全是热血,还有冰冷和残酷。你们是英雄,同胞需要你们英雄下去。
最尴尬的是,电影院的观众们,此时也是在“看”。
有意无意地,他们被迫分享租界看客们的视角,以及那种事不关己的地位处境。
于是这感动和煽情中就带着刺,引人不安,以至于不得不反省自己为英雄牺牲精神而感动的行为里,是不是也有着某种不道德?
毕竟,租界看客们固然冷漠,可他们却仍在战火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被烧到,而电影院里的我们,却是处在被拿着望远镜的教授更远的地方啊。
戏
有看,就有戏。
四行孤军的斗争,在整个上海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可以说并无太多战略意义。蒋委员长和国府之所以让他们以要离、荆轲的姿态把戏演下去,把命豁出去,是为了争得国际友人的同情,以明国人奋战和牺牲的决心。
布鲁塞尔会议的延宕令这种表演连政治层面的意义也失去了,牺牲失去了意义,成为纯粹的戏。
管虎似乎是一位非常喜欢刻画“无意义的斗争”的导演,这里面甚至还颇有一些中年危机式的焦虑。在《老炮》里面,他为六爷安排的那场茬架的戏,露骨且过火,从而令这位过时的话事人不像是昔日的街头大哥,而更像是热衷于唱堂会的疯子,于是这场戏不光没有令一次无意义的斗争崇高化,反而显得矫揉造作,甚至于矮化了六爷的形象,令他于过时和碎叨之外,平添了一份自我感动式的尴尬。
四行孤军里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遭遇,接到上峰撤退的命令后,谢团长也需要为自己的斗争重新寻找意义。
于是在这个时候,演戏不再是表演给国际友人看,而是为长养国人志气,撒播斗争的决心和种子。
这显然既不合历史的逻辑,也不合故事的逻辑。
历史上抗战的成功,并非因为几个英雄的示范(否则抗战也太容易成功了),而是成功于对敌我势力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此的持久战。
国民启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且这种启蒙,不可能是引刀成一快式的无谓牺牲。
而倘若按照事实的逻辑,看客们的几声叫好,教授奋激而起的几响零星枪声,戏台上的一出长坂坡,乃至于街头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所有这些行为加起来,恐怕也仍不足以支撑起“国民抵抗之志气被唤起”这一宏大命题,这也就让谢团长的行为遭遇了六爷式的尴尬:
塑造这个角色时,导演不得不靠一种英雄主义的、不乏自我感动的激情,去解释其间的落差。充满弹孔的旗帜,一轮又一轮惨烈的对抗,乃至于空洞的政治宣言,都被用来掩饰叙事的断裂和逻辑的不自洽。
在这里姜文就比较鸡贼,他始终让故事局限在土匪打恶霸这么一个具体微观的事情上,意义怎么赋予,打到铁门上的几个弹孔意味着什么,不妨交给观众。
你说我讲的是土匪打恶霸,那故事本体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还有言外之意皮里阳秋打一动物,那随便咯,看你怎么想吧。
二者互相对比,或可见出管虎的得失。
马
导演好像挺喜欢拿动物说事儿。《斗牛》里是头牛,《老炮》里是只鸵鸟,到了《八佰》则成了一批白色的骏马。
在三部不同作品里,动物都具有象征色彩,并不赋予了各自不同的意义。相同的地方,是它们都站在一个跟人对比的位置,以暗示读者:动物是这个样,人活的是那个样。
六爷放走鸵鸟,里头就很有精神寄予的色彩。他活得不舒展,看动物也不舒展他就不痛快,所以想让动物替自己舒展。
尼采抱马而哭的故事果然很有感染力,这招也被管虎学到了。
《八佰》里这匹马同样承载了很多东西,这匹马纯白无一杂色,充满着高贵和昂扬的气息。战争打了过来,主人不见踪影,他和这里的人民一样遭受战火洗礼,不同的是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精气神。
后来谢团长和日军长官见面,日军骑黑马,为了不输阵,这匹白马成了谢团长的坐骑。于是写马,就是写人,所谓人靠衣裳马靠鞍,说得是一件事情。
而在更多的时候,白马则是充当着小湖北的梦想,在那个梦想里,赵子龙骑白马,在曹军阵营七进七出,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的护国将军。于是马,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
最后,说下整体印象。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导演想讲述一个斯皮尔伯格式的故事,不光说战争,更要讲人性。只不过他又想迎合市场,搞财富密码,又心有不平,想批判些什么,最后没搞成《辛德勒的名单》,也没够到《拯救大兵瑞恩》,倒是炮制出一个不合时宜的《智取威虎山》。
单纯说作品,《八佰》比智取威虎山好看,加上不合时宜,估计就打平手吧。
保险经纪人凯鹅,感谢阅读,如咨询保险,可扫二维码
会员全站资源免费获取,点击查看会员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