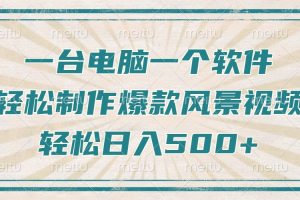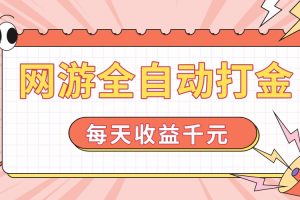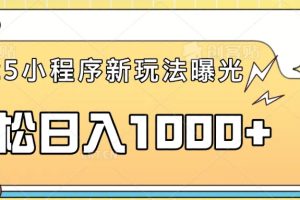发现思想力成就影响力

如果你认为“三年高考两年模拟”是一种负担,那“学习”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负担。
一
经过多年观察,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当我们谈到某个社会问题成因的时候,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因方面的,比如体制、规则、环境之类;另一种是内因方面的,比如自己没天赋、不努力、眼界差、不善于发现和抓住机会等等。
如果两篇文章说同一个问题,一篇主要说外因,另一篇主要说内因,那一定是后面那篇的阅读量高。
为什么呢?我猜,主要原因也有两个:第一,外因一般比较复杂,不容易理解;第二,外因一般比较复杂,不容易改变。既然理解不了、理解得了也改变不了,谁还转呢?
何况转这样的东西还容易得罪人——你怎么知道,看你朋友圈的人里,没有你转的文章所批判的对象。
那还不如转几篇“自我反省、自我提升”的鸡汤实在。虽然,整天在朋友圈里发鸡汤文的人,不一定整天按鸡汤文的标准去做,但这种行为至少可以让自己看上去勤恳踏实、不怨天尤人、浑身正能量。
要知道,“内省”可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基本上,大家对所有问题的态度都是这样。
可能,只有教育问题是个例外。

二
五年前,我是“快乐教育”的坚定支持者。
我像大部分人一样,认为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学生没天赋或者不努力,而是现行教育体制出了问题。这时候,我们就不像对别的问题那样,强调“内因是主要方面”,而是指责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扼杀了未来的花朵。
最让我痛恨的无疑是“应试教育”:因为我们在设计规则的时候,把“考试”当成了阶层攀升的唯一途径,导致大家都忘记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国民的独立思考和健全人格;因为考试必须设置“标准答案”以保证公平,导致每个人的思维都被束缚,不懂得如何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现在,我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不再痛恨“应试教育”了。
大概是在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的时候吧。
如果没有“应试教育”,我甚至可能没法上大学。要真是那样,我恐怕也就没有机会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
换句话说,“原生家庭”给不了我的东西,恰恰是“应试教育”给了我。
于是,我猜测,也许并不是我们故意把考试“设计”成了阶层攀升的唯一途径,而是目前我们还没找到更好的途径。

三
我是从一个单亲家庭长起来的。母亲是临时工,工资常年维持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0%—50%的水平上。
母亲尽可能不让我吃苦。然而可想而知的是,当同学们车接车送的时候,我只能走路上学,当同学们路边吃麻辣串的时候,我只能跟着他们蹭吃蹭喝,当同学们用随身听和MP3听周杰伦的时候,我只能听他们的翻唱版。
怪不得直到今天,我都觉得《简单爱》听上去很复杂。
但我一点也不自卑。那时候,我学习很好,脾气也不坏,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同学们也乐意选我做班干部,在学校里混得风生水起。
当然,老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永远不可能对每个学生完全一视同仁。如果他们偏爱那些学习好的学生,那对学习不怎么好的学生来说,这就涉嫌“歧视”。
然而我总觉得,若“偏爱”是个注定发生的事,“偏爱学习好的学生”似乎比“偏爱家庭条件好的学生”稍微公平一些。
毕竟前者至少是以学生的个人能力为依据的。

四
何况,我的老师们始终在朝公平的方向努力着。
他们对每个学生都很严格。他们不停地布置一堆作业三的英语单词,不停地开家长会,不停地家访,从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差生”。
他们还经常做一些过分的事,比如总是找理由让体育老师“请假”,或者干脆让美术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听写英语单词。
美术老师好像还挺乐意做这种“兼职”。我当然不乐意,于是以偷懒来进行“消极抵抗”,比如老师让每个单词写四遍,我却每隔一两个单词少写一遍。
英语老师居然立刻发现了这件事。她一个人要看两个班120多份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作业,我真不晓得她是怎么做到的。
她罚我站了两节课,然后每个单词重写八遍。我说我可是英语课代表啊,她点点头说,哦哦,我倒忘了这茬,那就每个词写十遍吧。
直到今天,我母亲依然怀念那些老师。
“我从来没操心过这孩子的学习,都是他老师看着他学的。”她总是这样对别人说。
我说你怎么不说这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呢,她白我一眼:“你快拉倒吧。要不是你高中老师最后松下来,你高考也不至于考得那么差。”

五
我高考发挥确实不好,以至于只能上一个普通的985高校。然而我从不把这件事跟我高中的教育水平联系起来,因为它已经是我们省最好的高中之一,而且很多人认为“之一”也可以去掉。
发挥不好,是我自己的心理素质问题。大概正因如此,我才会觉得“素质教育”好重要。
当然,我也得承认,我上高中那会儿,“减负”思潮对老师们的影响已经比较深了。但就算是这样,我也只能说“高中”并不是一个强调“减负”的好时机,因为它容易导致我这种自律能力差的学生迷失方向。
这可不是哪个老师的问题。就像有人抱怨“现在的老师不像从前那样负责”一样,这其实不足以说明老师普遍比以前差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对他的影响。老师也一样。
不过话又说回来,“自己的孩子不努力,却抱怨老师管得不严”,也不能说是错的。因为“学习”本来就是桩苦差事。
没几个未成年人能仅靠“兴趣”或“理想”保持长达12年的勤奋学习状态。“头悬梁锥刺股”根本不是人类的天性。
你们说我说的对吗,各位成年人。
如果你认为,在孩子还没有被生活的切肤之痛灼伤之前,不要先用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垮他,那么其实你已经做出了预设:你的孩子永远不会触碰到生活的切肤之痛。
否则,你赞成“减负”,就是嫌他痛得轻。

六
在一个人多资源少、分配机制不完善的地方,“负”是很难被真正减掉的。当我们表面上减掉了学校的“负”,这个“负”其实转移到了家长身上。
家长当然也可以不承担这个“负”,但那就等于让未来的孩子自己承担。一般的家长恐怕狠不下这个心。
于是我们看到,“减负”之后,有本事的家长往往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学习,或者给孩子请私教;有时间的家长则要花更长的时间陪孩子学习,甚至自己跟孩子一起重新念书。
这些家长很清楚:一旦孩子在10岁的时候接受了“快乐教育”,20岁的时候会很苦恼。
可能,那些极有本事的家长除外。比如有些家长,就算他的孩子连100以内加减法都不会,他也能给孩子弄个企业董事长干干。但就算是这些人,他也很清楚:如果自己希望孩子青出于蓝,还是不能搞“快乐教育”。
我不是说“教育”一定不应该“快乐”。然而快乐也分两种:上KTV随便喊两嗓子放松放松,是一种快乐,经过10年专业训练然后登台演出捧格莱美奖,也是一种快乐;找块草坪随便踢几脚球发泄发泄,是一种快乐,每天坚持跑12公里然后驰骋绿茵场拿大力神杯,也是一种快乐。
相信大家都听过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也许“画画”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但“画鸡蛋”显然不是。可他又不得不坚持画鸡蛋,因为不这样做,就只能获得前面那种很容易、很痛快、但成就感很弱的快乐。
而我们想要哪种快乐呢?很多时候,我们呼吁减掉的“负”,恰恰是“画鸡蛋”。

七
当我们发现“周围的人都在批判应试教育”,也就跟着批判,发现“大家都在呼吁减负”,也就跟着呼吁。可这到底对谁有利呢?
如果真的要给学生“减负”,那应该给他们的一生“减负”,特别是减少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而不是只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减负”。
这当然很难,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似乎不该向相反的方向走。
我猜这可能算是一个基本原则:减掉负担的同时,不该把希望一起减掉。
会员全站资源免费获取,点击查看会员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