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家是领导,是权力的化身,你想混下去,就必须用行动来宣誓效忠:喝酒。
喝得越恶心,越醉,丑态出得越多,代价越大,就越能表达,你对他的无条件认可与服从。
而周围所有人,则是这场仪式的见证方、主持人。
通过这种方式,领导确权完毕,才会心中暗爽,对你放下戒心。
也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你喝的不是酒,而是向权力跪拜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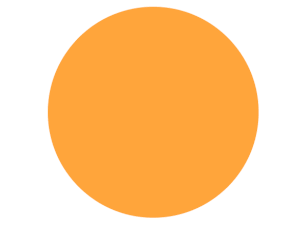
在《1984》里,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曾亲口对温斯顿说:“这将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胜利的世界。”
至于恐怖的理由,其解释是:
一个人如何用权力来控制别人?
对,让他受苦。
服从并不够,除非给他苦吃。
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组合成新的思想……
因此,当一个国家越专制,权力越集中,监督越少,受苦受辱的人就越多。
不仅在工作中,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投注在酒桌上,就成了肆无忌惮的逼与被逼灌,灌与被灌。
这种社会里的小人物,根本没有反抗的可能,只有通过干杯,向上级表达这样的信息:
虽然我知道这是受虐,你知道这是施虐。但是,我接受。
我接受你伤害我。
我接受你虐杀我。
为了你,我牺牲自己的身体,亦在所不惜。
这是我向你纳的投名状。
这是我对自己忠心的证明。
是的,我就是帮你拎包的人,你的随从,你的奴隶,对你唯命是从没有二心的仆人。
而这,正是集权统治的基础:在权力面前,我们不是人,我们没有独立意志,我们甘愿听从于你,为你付出一切,让你统治更稳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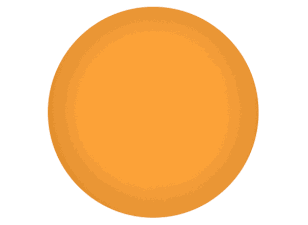
大象公会在2014年,做过一期文章,研究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最能喝?
结论很妙:官本位思想特别重的地方,人的酒量都特别大。
比如,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
黑龙江人比广东人能喝。
内蒙古人比上海人能喝。
这和体质无关,和体制有关。
体制化最低的东南沿海,官本位思想较淡,契约精神比较浓,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主流社会不但没形成像样的酒桌文化,甚至朝着悖离中国酒文化的方向发展。
当然,北京是一个例外。
权力中心,官员扎堆,没人敢随意造次。
等级制森严的环境,劝酒对所有人都是极大负担。
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在作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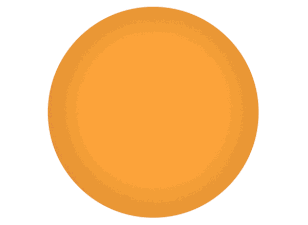
我真的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疯狂灌酒的人。
直到今天,我依然对多年前被灌下的酒耿耿于怀,恨不得时光逆转,拎着酒瓶,爆了灌酒者的头。
这些人,要么是领导,要么是粗俗的商人。
领导喜欢服从,商人喜欢诚意。
如何表达诚意?
除了空口白话,你还得缴纳一定的抵押物,来证明你的态度。
这不是钱,不是承诺,而是丑态。
因为,之于一个正常人,面子、尊严、风度,都是我们最看中的。而酒场就要求你丢弃这种重要的东西,喝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他看到你的丑态,才会放心,认为你没有防着他,合作关系才能再进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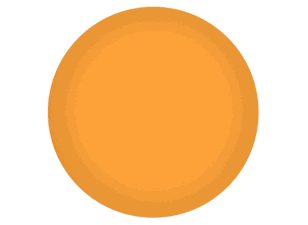
如前文所言,一个酒场,只有暗含权力与利益,就一定不再纯粹。
它不再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浓情蜜意;
也不再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快意淋漓。
而是“项伯帐中姻汉祖,吴钩碎斗鸿门宴”式的角斗场、利益场、宣誓场。
这种机关重重,不能自主的酒席,自然变得令人骇怕,自然令人感叹,“谁想应酬?无非是为稻梁谋!”
中国确有很多人,确实喜欢饮酒。
比如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再如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但这种饮,都是自由选择,而非被迫为之。“我要喝”,和“要我喝”,区别还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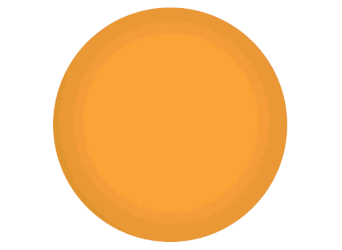
会员全站资源免费获取,点击查看会员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