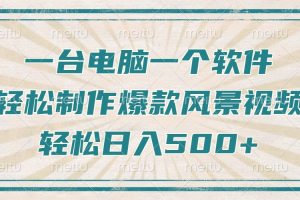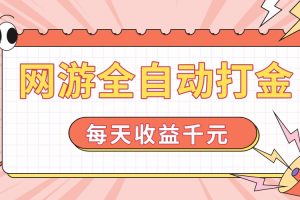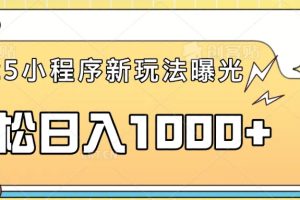纯粹的人和纯粹的生活
文/徐济成
在我众多媒体和体育圈朋友中,余耕是一个矛盾体,他是一个由各种反差构成的男人。像大漠中的一棵柳树或者沧海中的一艘画舫。

把余耕放在普通人中,他是一个大个子;把余耕放在篮球场上,他就是一个小个子。他本应该是像纳什一样去打后卫,但是他更喜欢像奥尼尔或者霍华德一样,到巨人如林的篮下去腾挪扑杀。在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对手中间,余耕像是翻山越海不知疲倦的夸父,时隐时现,一往直前。
我和余耕是在首都记者教练篮球队中认识的。这支有24年“光荣历史”的篮球队是由首都的篮球记者和体校、北京队、八一队的教练共同组成的。在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这支特殊球队中,余耕要算第四代球员,一个新兵和小字辈,他是这支球队激情与活力的象征!每次我们球队抢到篮板球,余耕总是第一个冲到对方篮下的那个人,他的速度之快,往往让十五、六岁的首钢少年队小伙子们望尘莫及。在我认识他的这七、八年中,他的速度好像从来没有降低过,上周和首钢少年队打完比赛,他竟然向我们展示了一肚子错落有致的腹肌块儿。在我们这支以中老年人为主组成的篮球队中,腹肌绝对是极为罕见的奢侈品。

在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固定在篮球场之前,余耕是专业赛艇队队员,他不但有傲人的腹肌,还有宽阔的背肌。但是在被八一赛艇队选中之前,他是青岛一所业余体校篮球队的前锋,如今打篮球算是他回归本行。生活中的余耕基本如他在球场上的作风,是一个雷厉风行,勇往直前的人。但是浓眉大眼的余耕绝对不是一个五大三粗、四肢发达的粗人,实际上,第一次见到余耕的人,都不会把他和运动员联系在一起。如果回到唐宋时代,他绝对是秦琼或者林冲那一类儒雅内敛的武林高手。比如在比赛中每次快攻上篮得分,或者在篮下用“梅花步”把对手晃晕之后,余耕常常会摇头低眉一笑,好像是对人家做了件不好意思的事情又不便直接道歉。
去年余耕就告诉我,他有一部小说要脱稿,我就一直像盼着自己侄子出生一样等着这部小说的问世徐济成,终于我在奥运会之后看到了小说的全部。这是一部极为别致的作品,小我近十岁的余耕,是新一代媒体人中的佼佼者,从报纸到杂志,从电视到网络,从篮球到高尔夫,都是他发动快攻或者腾挪扑杀的球场,对于社会的剖析和对于人的了解,余耕这一代“多媒体人”要远远深刻于我们这一代在一个单位老死终生的“单媒体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余耕都有自己的朋友。记得三年前我们记者教练联队去河南打比赛,在熙熙攘攘的郑州火车站,余耕对我说,中国的火车站绝对是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奇人怪事。所以,我一点都不奇怪,余耕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
《德行》里面的人和事儿都是余耕熟悉的,所以他在《德行》中嬉笑怒骂、冷嘲热讽,都能信手拈来。十多年的传媒从业经历,使他能够全方位来审视这个群体。有些人因为熟知而麻木,可余耕却在熟知之后进行反思,这是难能可贵的。余耕还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德行》里向读者展现了他所钟爱攀岩运动,我虽然从未尝试过这项男人的运动,但在读完《德行》之后也忍不住“聊发少年狂”。

诗有二十四品,男人也有二十四品。余耕是一个身兼数品的男人:虽不豪放,但不失雄浑,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虽不含蓄,但处处自然,如逢花开,如瞻岁新;余耕经历了这个大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百味,但依然清奇、洗练,落落欲往,矫矫不群;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对朋友和生活拥有不变的浪漫和率直。去年他一度到山东青岛发展,但是割舍不下我们的篮球队和这一群相识多年的朋友,于是常常一人打“动车组”回北京,就为周五下午那一场十年不变的比赛。
认识余耕就像认识生活一样,在种种看似矛盾和反差的表象之后,你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男人和纯粹的朋友。
(文章获当事人余耕老师授权)
这是一个有态度,有温度的篮球平台
这里愿意记录你的篮球故事
这里分享快乐篮球
长按上图,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会员全站资源免费获取,点击查看会员权益